目录
快速导航-
星青年 | 白昼正缓慢消失(组诗)
星青年 | 白昼正缓慢消失(组诗)
-
星青年 | 骑鱼的人(组诗)
星青年 | 骑鱼的人(组诗)
-
星青年 | 阳光雨露(组诗)
星青年 | 阳光雨露(组诗)
-
星青年 | 江水奏响的万木(组诗)
星青年 | 江水奏响的万木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截止此时的天空(组诗)
文本内外 | 截止此时的天空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诗是一件经由个性过滤的事情
文本内外 | 诗是一件经由个性过滤的事情
-
文本内外 | 孔雀羽毛(组诗)
文本内外 | 孔雀羽毛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
文本内外 |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
-
星现实 | 怀念一只小鹿犬(外二首)
星现实 | 怀念一只小鹿犬(外二首)
-
星现实 | 在我和铲具之间(组诗)
星现实 | 在我和铲具之间(组诗)
-
星现实 | 暮色里(组诗)
星现实 | 暮色里(组诗)
-
星现实 | 午夜场(二首)
星现实 | 午夜场(二首)
-
星现实 | 听诊器里的蝴蝶(组诗)
星现实 | 听诊器里的蝴蝶(组诗)
-
星现实 | 约等于零(组诗)
星现实 | 约等于零(组诗)
-
星现实 | 最后一课(组诗)
星现实 | 最后一课(组诗)
-
星现实 | 爱的置换(组诗)
星现实 | 爱的置换(组诗)
-
人间书 | 苍山负雪(组诗)
人间书 | 苍山负雪(组诗)
-
人间书 | 宁 夏(组诗)
人间书 | 宁 夏(组诗)
-
人间书 | 一片云垂向入海口(组诗)
人间书 | 一片云垂向入海口(组诗)
-
人间书 | 春天的三重赋格曲(组诗)
人间书 | 春天的三重赋格曲(组诗)
-
人间书 | 晚宴(组诗)
人间书 | 晚宴(组诗)
-
人间书 | 石头记(组诗)
人间书 | 石头记(组诗)
-
人间书 | 鸟巢像一只眼睛(组诗)
人间书 | 鸟巢像一只眼睛(组诗)
-
人间书 | 鸟鸣啄破黎明的时辰(组诗)
人间书 | 鸟鸣啄破黎明的时辰(组诗)
-
山河志 | 大雪复调(组诗)
山河志 | 大雪复调(组诗)
-
山河志 | 夜宿汪湖(组诗)
山河志 | 夜宿汪湖(组诗)
-
山河志 | 不败的鲜花(组诗)
山河志 | 不败的鲜花(组诗)
-
山河志 | 白云之下,大地之上(组诗)
山河志 | 白云之下,大地之上(组诗)
-
山河志 | 大凉山,不是一座山(组诗)
山河志 | 大凉山,不是一座山(组诗)
-
山河志 | 湘情之恋(组诗)
山河志 | 湘情之恋(组诗)
-
山河志 | 域外生活(二首)
山河志 | 域外生活(二首)
-
实力派 | 石木集(组诗)
实力派 | 石木集(组诗)
-
实力派 | 去菜园小记(外二首)
实力派 | 去菜园小记(外二首)
-
实力派 | 另一种意义上的海(外二首)
实力派 | 另一种意义上的海(外二首)
-
实力派 | 风吹拂着远行者的衣襟(组诗)
实力派 | 风吹拂着远行者的衣襟(组诗)
-
实力派 | 苍耳子(组诗)
实力派 | 苍耳子(组诗)
-
实力派 | 对板栗树的描述(组诗)
实力派 | 对板栗树的描述(组诗)
-
实力派 | 安静的下午(外二首)
实力派 | 安静的下午(外二首)
-
压轴 | 群山的声音(组诗)
压轴 | 群山的声音(组诗)
-
星干线 | 孤独阐释一种固执(外一首)
星干线 | 孤独阐释一种固执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听一位装修工讲那时乡下的黄昏
星干线 | 听一位装修工讲那时乡下的黄昏
-
星干线 | 向一群藤蔓致敬
星干线 | 向一群藤蔓致敬
-
星干线 | 路
星干线 | 路
-
星干线 | 灯笼草
星干线 | 灯笼草
-
星干线 | 大 象
星干线 | 大 象
-
星干线 | 蜉 蝣(外一首)
星干线 | 蜉 蝣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南 词
星干线 | 南 词
-
星干线 | 新年的一次相见
星干线 | 新年的一次相见
-
星干线 | 清 明
星干线 | 清 明
-
星干线 | 迁徙的鸟
星干线 | 迁徙的鸟
-
星干线 | 知更鸟
星干线 | 知更鸟
-
星干线 | 盐鸭蛋坛
星干线 | 盐鸭蛋坛
-
星干线 | 一封信(外一首)
星干线 | 一封信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听水声(外一首)
星干线 | 听水声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巉 岩
星干线 | 巉 岩
-
星干线 | 序 曲
星干线 | 序 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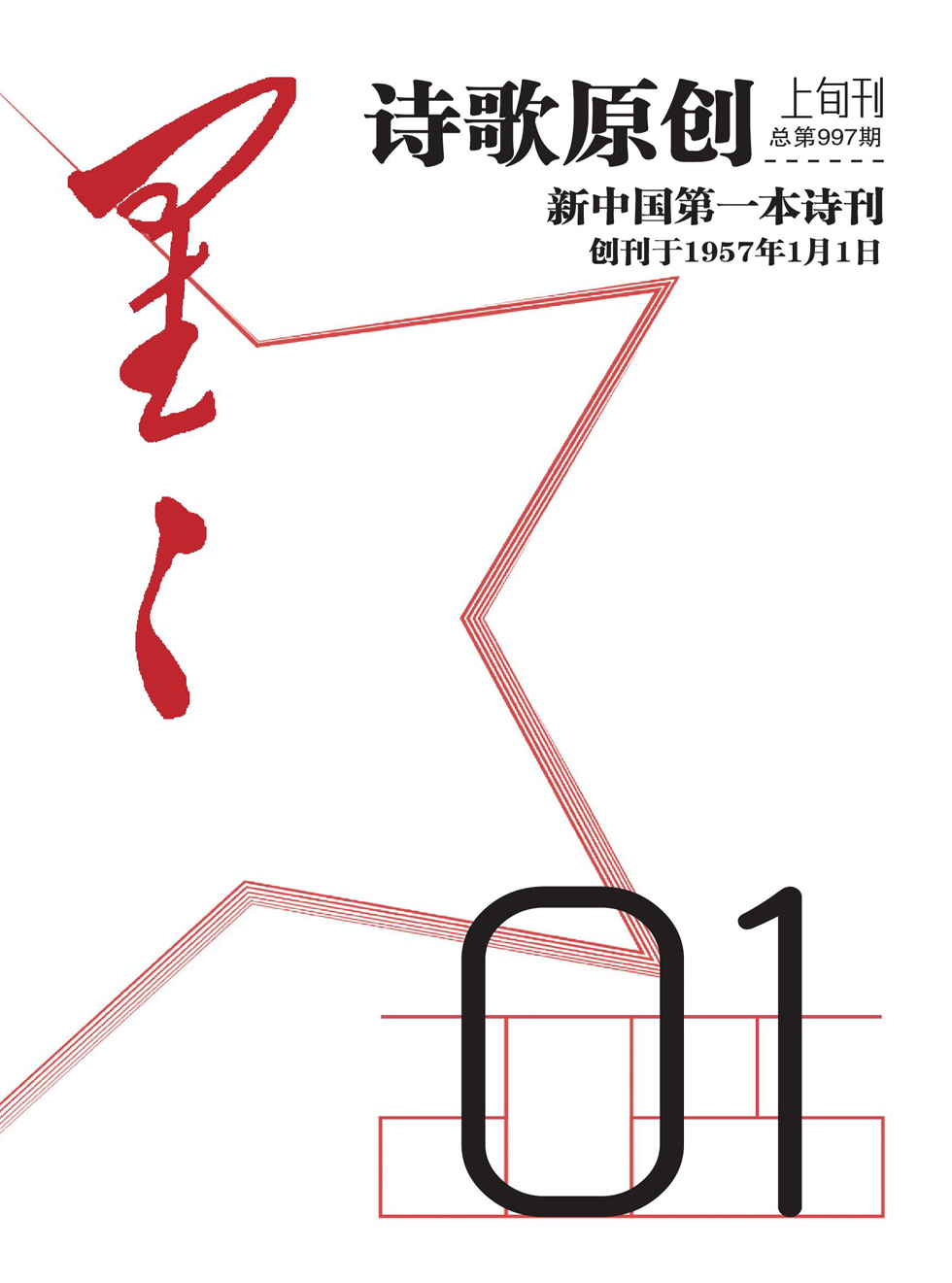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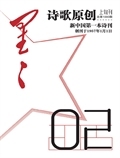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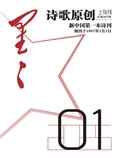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