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
特稿 | 龙舞南北极
特稿 | 龙舞南北极
-

中篇小说 | 倒宝壶
中篇小说 | 倒宝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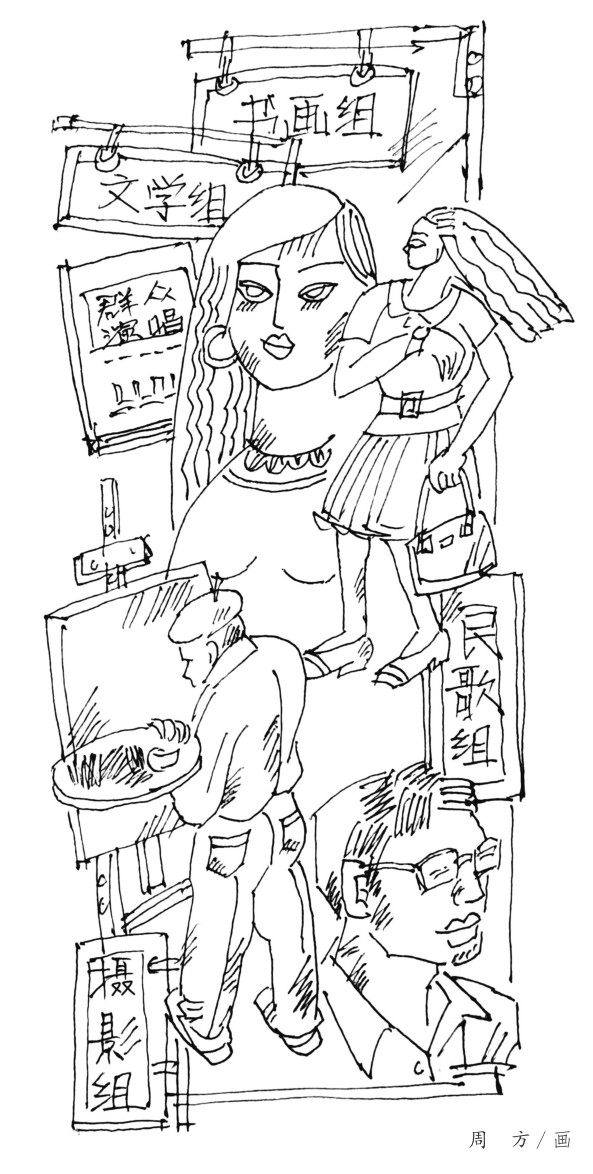
短篇小说 | 文化馆
短篇小说 | 文化馆
-
短篇小说 | 筷 乐
短篇小说 | 筷 乐
-
新声 | 夏 市
新声 | 夏 市
-
新声 | 黔北暮歌
新声 | 黔北暮歌
-
新声 | 故事从寨门前启程
新声 | 故事从寨门前启程
-
新声 | 述往思来的哀悼书写
新声 | 述往思来的哀悼书写
-
烟台故事 | 绒 绣
烟台故事 | 绒 绣
-

散文随笔 | 缓 归
散文随笔 | 缓 归
-
散文随笔 | 死锅塌
散文随笔 | 死锅塌
-
散文随笔 | 莼 思
散文随笔 | 莼 思
-
诗歌 | 幸福之境(组诗)
诗歌 | 幸福之境(组诗)
-
诗歌 | 高处的炊烟(组诗)
诗歌 | 高处的炊烟(组诗)
-
诗歌 | 落满人间(组诗)
诗歌 | 落满人间(组诗)
-
诗歌 | 吊脚楼是我们的家(长诗)
诗歌 | 吊脚楼是我们的家(长诗)
-
诗歌 | 短诗小辑
诗歌 | 短诗小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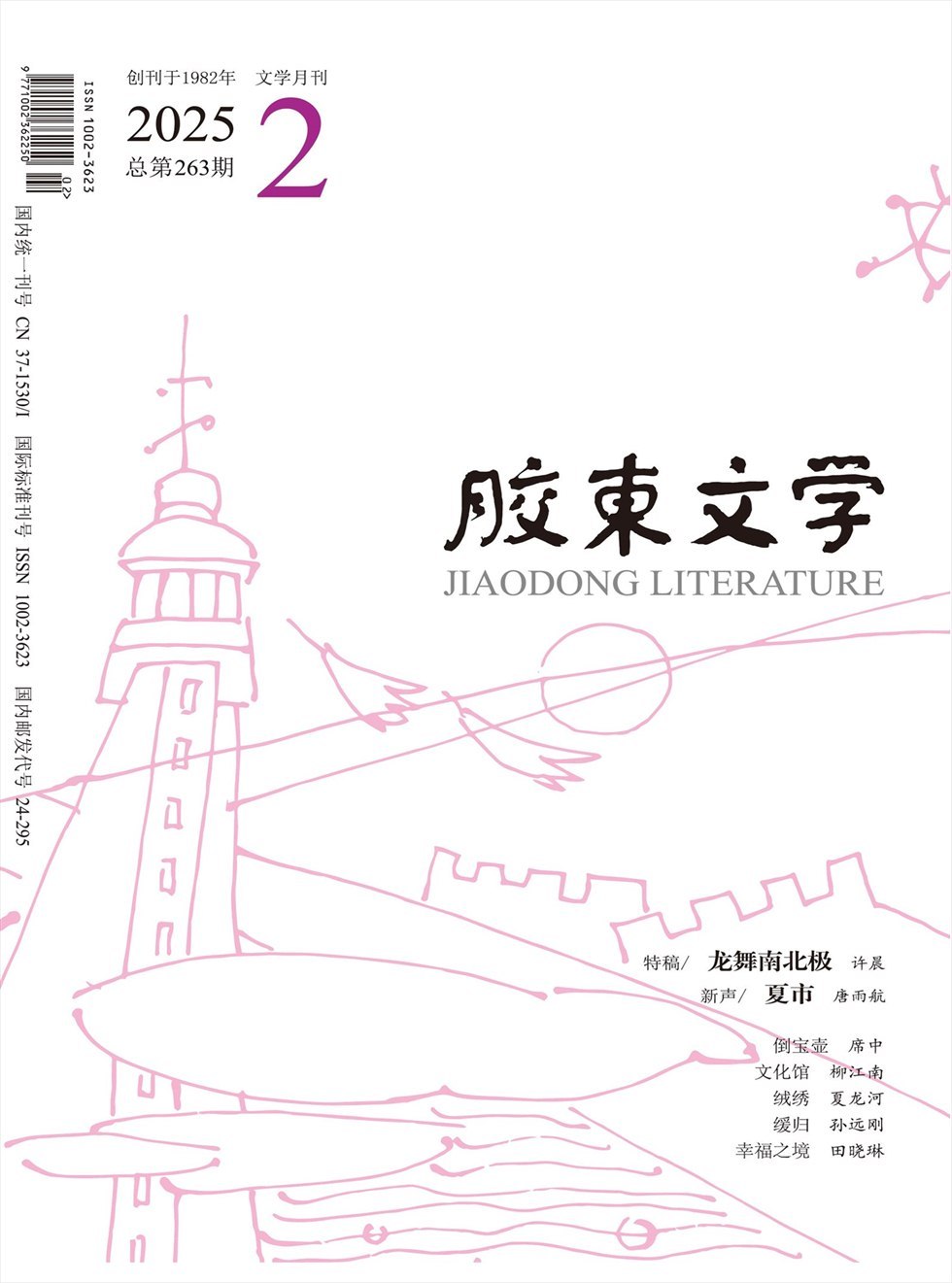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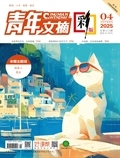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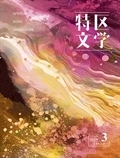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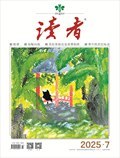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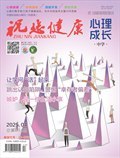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