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解释与重建 | 书与城市
解释与重建 | 书与城市
-
解释与重建 | 上杭之夜
解释与重建 | 上杭之夜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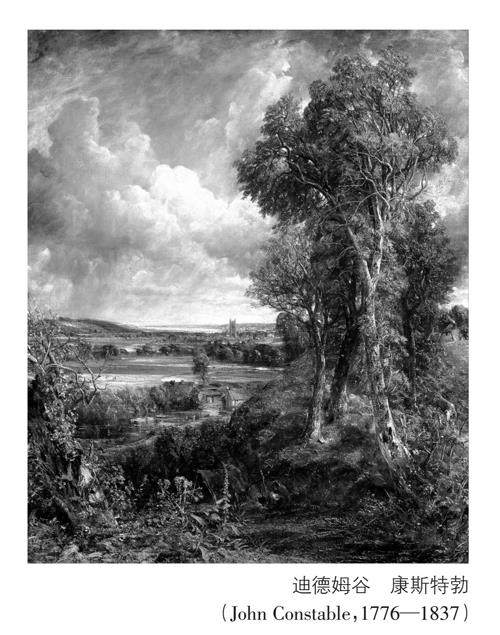
解释与重建 | 巨石阵:史前艺术漫步
解释与重建 | 巨石阵:史前艺术漫步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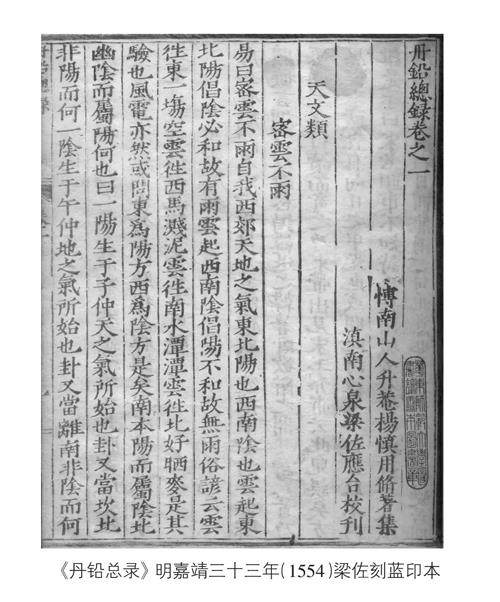
解释与重建 | 鬓有丝集
解释与重建 | 鬓有丝集
-
解释与重建 | 母亲
解释与重建 | 母亲
-
解释与重建 | 枪
解释与重建 | 枪
-
解释与重建 | 看他们点起了火把
解释与重建 | 看他们点起了火把
-
生活志 | 且慢
生活志 | 且慢
-
生活志 | 面色
生活志 | 面色
-
生活志 | 小明同学
生活志 | 小明同学
-
看·听·读 | 赠书与买书
看·听·读 | 赠书与买书
-
行旅 | 衙前井
行旅 | 衙前井
-
行旅 | 漩涡镇
行旅 | 漩涡镇
-
闲话 | 树下二记
闲话 | 树下二记
-
闲话 | 桐树、桐油和童便
闲话 | 桐树、桐油和童便
-
闲话 | 青草的气息
闲话 | 青草的气息
-
闲话 | 春食于野
闲话 | 春食于野
-
行旅 | 衙前井
行旅 | 衙前井
-
行旅 | 漩涡镇
行旅 | 漩涡镇
-
闲话 | 树下二记
闲话 | 树下二记
-
闲话 | 桐树、桐油和童便
闲话 | 桐树、桐油和童便
-
闲话 | 青草的气息
闲话 | 青草的气息
-
闲话 | 春食于野
闲话 | 春食于野
-
生活志 | 且慢
生活志 | 且慢
-
生活志 | 面色
生活志 | 面色
-
生活志 | 小明同学
生活志 | 小明同学
-
专栏 | 首尔咖啡处处
专栏 | 首尔咖啡处处
-
专栏 | 缝缝补补好习惯
专栏 | 缝缝补补好习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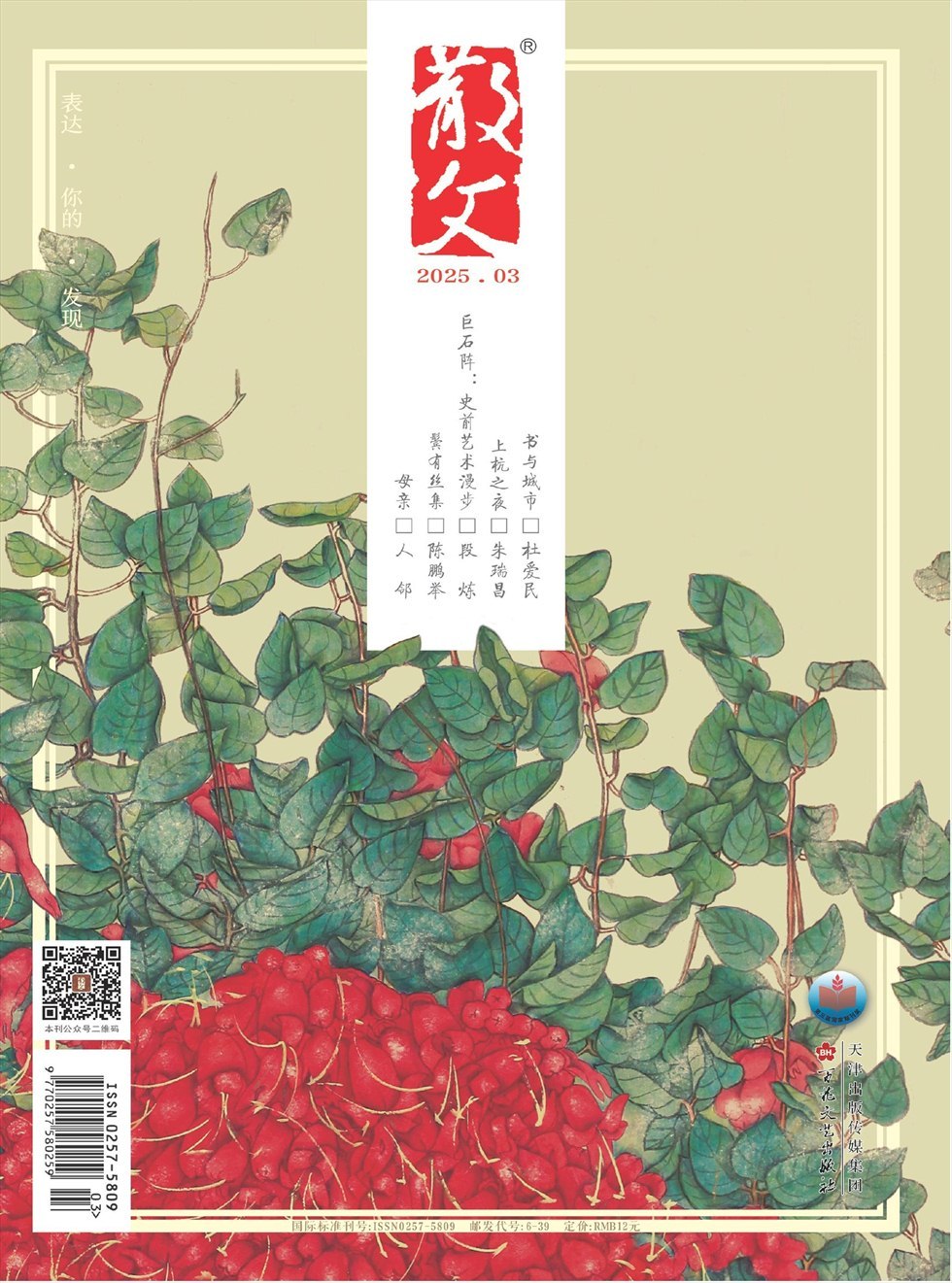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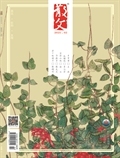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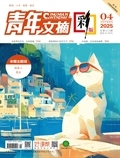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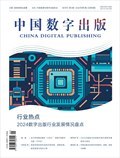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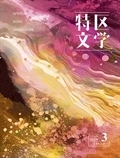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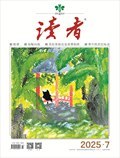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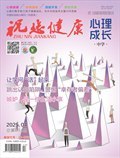


 登录
登录